发现古典植物世界的诗意(创作谈)
发布时间:2024-11-05 17:30:18 来源: sp2024110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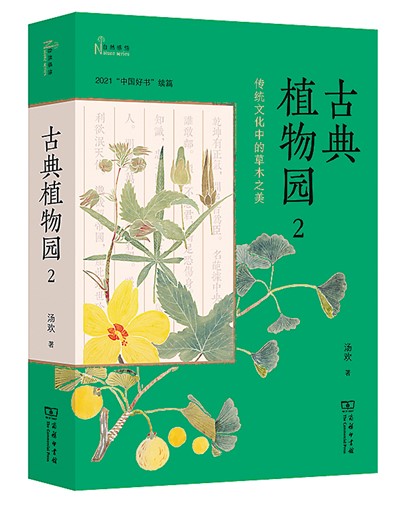
生长于草木繁茂的乡间,我自幼对身边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,囿于条件有限,彼时尚不知那些自由绚烂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。大学上《诗经》课,接触到细井徇《诗经名物图解》,看到那些精美的插图,才真正认识了荇菜、飞蓬、游龙(红蓼),然后再读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“山有乔松,隰有游龙”“自伯之东,首如飞蓬”,这些植物立即浮现眼前。2000多年前,先民怎样发现它们,为何将它们写入诗中?经过漫长的历史流转,它们又寄托了后人怎样的情感,发生过哪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?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开始以具体的植物为对象,去探寻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。翻阅古籍中与植物相关的各类文献时,我越发觉得,植物是打通古今、连接中西的载体,我们身边寻常可见的一草一木,背后都可能蕴含着无比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自古以来,植物就是衣食、医药之源,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;与此同时,山中乔木、河畔青草、空谷幽兰,亦是先民寄情寓兴的重要载体。牡丹象征富贵,兰花是君子,梅花有傲骨,折柳赠远别,红豆寄相思,它们出现于文学、绘画之中,是融在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。如果植物会说话,讲起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遭逢和际遇,可供言说的很多:从本草、农学、园艺,到经学、文学、民俗、掌故,乃至东西文明交流、历史地理气候……可以说,由草木汇集起来的,是一个丰富驳杂、有趣有料、诗意盎然的世界。
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那么美,与它们相关的诗文典故那么美,画家笔下的花卉、博物插画和本草图谱也是那么美,如此多美丽的事物涌现在我面前,除了将它们写下来,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感动。“写作是内心的需要”,我在中文系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,贯穿了两本《古典植物园》写作的心路历程。
因此,《古典植物园》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写。美国小说家卡佛说,每个作家都应该写自己熟悉的、能感动自己的事情,而不是写“应该感动”他的东西。我在选取所要写的植物时,就遵循了这一原则。
写哪种植物往往缘于一种契机,或一种缘分。这个契机可能是读书时遇到了问题,有了问题意识,才有了寻找答案的动力。例如,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里的“勺药”究竟是不是芍药?“蜀葵”是因为产自巴蜀而得名吗?木兰就是玉兰吗?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,正是写作的过程。
这个契机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的发现。一年冬天在北京的早市上,我见到了慈姑和荸荠,联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说,觉得有必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两种植物。之后重读汪先生的文章,竟然有意外的发现。又一年夏天去襄阳,在护城河的桥头被两棵巨大的夹竹桃所震惊,于是就想了解一下这种植物的前世今生。
另外还有一种契机,是某个时刻遇到了这种植物,而它勾起了我的过往回忆,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。例如《古典植物园》中的葎草、金银花、茉莉、水杉,是分别写给我的父亲、母亲、中学好友,以及纪念我外婆的。在写这样的文章时,情感自然流露,写起来最为顺畅。
《古典植物园》无意向读者做百科全书式的介绍。若是一味罗列文献、面面俱到,与古代类书又有何异?因此,有了写作的契机之后,扎进书堆,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有用的资料,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。这项工作有时无比繁琐,如果遇到植物名实不符需加考辨,写作难度则会更大。
困难虽有,但在经史子集和东西文化之间寻找答案、挖掘故事,很像探险。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文献资料,不知道会有怎样令人心神荡漾的意外发现。
以《古典植物园2》为例,从杏花写到巴旦杏,才知道梵·高那幅著名的《杏花》是巴旦杏花,与我们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;在了解荸荠的外形、生存环境和文化特质后,对《受戒》这篇小说的鉴赏又多了一个视角;写冰雪中盛开的款冬,经由“僧房逢着款冬花”这首诗,对晚唐诗人贾岛有了颠覆性的认识;由蜀葵写到向日葵,得知它在传入我国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被嫌恶;而探索凤仙花、散沫花这两种可供染色的指甲花,就像在古印度、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间畅意神游……
每到这个时候,我都会真心认同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这番话:“有时候,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,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,会发生过去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。这时候,你才会感到,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。”
能够带给你“探险”般的乐趣,让你遇见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,这可能是两部《古典植物园》与其他植物文化类图书最大的不同。
(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)
(责编:王连香、李楠桦)